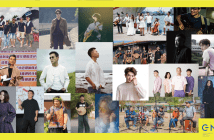趁著金曲獎結束沒幾天,我想說一個塵封多年的故事。
Shipy 是我們的前鍵盤手,第一代團員,直到 2008年夏天《晚安・巴士底》發行當天的演唱會上宣布離團。還記得 Shipy 是春佑在迴聲社隔壁的琴房發現的,在當時總是傳出憋腳流行樂鋼琴的琴房,那天有人在彈挺酷的爵士樂。印象最深的是,由於他看起來實在太臭屁,我們刁他說:「像〈Highway Star〉裡的風琴 solo 你彈得出來嗎?」他是第一次聽到那首歌但回說:「這蠻簡單的吧!」他立刻當場彈一了段,接著就被我們邀請進樂團了。
他很有才華而且很努力,我常覺得,他是我們所有人裡面最應該以音樂為志業的。他會寫歌又會編曲,鍵盤之外也很會彈吉他,過去很多大家熟悉的吉他其實不是我也不是冠文想的,而是 Shipy。比如〈煙硝〉、〈鐘聲行進〉、〈光腳狂叫〉等曲子,而像〈風車〉、〈佛陀〉這兩首複雜的木吉他曲,樂器的部分都是由 Shipy 一人獨自完成。還有一個很特別的,〈感官駕馭〉的 bass line 原型也是他想的。
第一張專輯發行後他就考到成大的研究所,離我們非常遠。但幾乎每個週末他都會搭客運上來,睡在頂樓工作室的沙發上,做好或編好一首歌再回去台南。這個習慣一直維持到他研究所畢業,到台北來工作。所以,即便我們第一張和第二張專輯中間隔了五年,但其實五年間他幾乎是用一種苦行僧的方式在做音樂,但我很深刻在其中感覺到愛與快樂。
Shipy 上來台北沒多久就結婚了,《巴士底之日》的製作期時,他在電子大廠上班,常常加班到十一點還要來錄音室錄音,有幾次我看他幾乎就要昏倒在鍵盤上了。有時熬夜到太晚,我們就直接睡在錄音室的木頭地板上,他連懷孕的老婆都來不及回去看一眼就又要出發去上班。那段時間很辛苦,大家都在燃燒生命撐著,但同時,對自己作品的自豪也是很巨大的,我記得專輯做好之後,他跟我說:「我覺得我們以後應該很難做出更屌的專輯了」,我都會心想,年輕人你才幾歲就講這種沒志氣的話。但現在想想,那些歌就是他生命中的純粹吧,他知道自己不會再有的。
《巴士底之日》發行後我們巡迴了一整年,唱了八十幾場,一點一滴的聚積了不少人氣,大家也都對於未來看到一些希望。但 2008 年五月,金曲獎的入圍名單公佈了,沒有回聲。對於當時已經拼了好幾年的命的我們來說,不在意是騙人的,但理智面也知道,獎這種事情真的不代表什麼,過了幾天心裡也就平靜了,直到在巡迴最終場前沒多久, Shipy 打電話給我。
他說,柏蒼,這幾年一邊玩團一邊工作真的體力不能負荷,加上現在除了自己還要照顧老婆兒子,我們也還想生第二個。玩團看起來真的很難生活啊… 但我當然也很愛音樂,所以我早在心裡跟自己打了個賭… 就是如果金曲獎得獎的話,我就繼續撐下去,沒得獎的話,我就好好回去工作照顧家庭… 嗯,所以現在,我想我要離開 ECHO 了…
這事已經過了很多年了,但依然是我心中的一個傷疤。我知道當年〈Dear John〉這樣快樂的歌推出時,有一些老歌迷不能接受。但其實,寫〈Dear John〉的時候我心裡是有一個聲音的,我一定要寫出一首超級厲害、所有人都聽得懂的搖滾樂,就當作是為了 Shipy。身為一個 band leader,我不想再有任何團員要因為現實的因素離開樂團…
Shipy 現在還是會不時帶著老婆和兩個小朋友來看我們的演出,偶爾也上台客串一下。我還是覺得他不應該在電子業工作的,但人生已經很難回頭了。他現在自己偶爾在林口辦小型表演做公益,一個人加一台鍵盤,上次還跟我說他想去考街頭藝人證。我聽到時心想,幹你的才華是可以做出很多屌歌改變世界的啊,你做這些但不玩團是三小。
沒有任何獎值得賭上人生,因為他們就是不值得。每個人的熱情、夢想、愛,都遠遠高過那些。
這首歌是我當年寫給 Shipy 的,〈狩獵霓虹〉
———
原文發表於回聲樂團 FB,經作者同意後轉載。